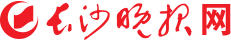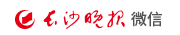散文 | 多面天心
■沐刃
來長沙二十多年了,,與天心的交集其實相對偏少——因為,,我工作和生活的空間,基本上在芙蓉,、開福一帶,。
1996年,,以前的“南區(qū)”改名天心區(qū),,其命名來由無疑與天心閣有關,。能夠以一地的名勝來為區(qū)劃命名,延續(xù)一座歷史名城的文化根脈,,連通歷史與當下,,構筑起共同的記憶與認同,這當然是幸事,,更是一樁美事,。
作為長沙僅存古城標志之一的天心閣,聲名自然響亮,,可我與它的第一次接觸,,卻已是來長之后的第七年——難道真如有人所說:對于身邊熟悉之地,我們往往以為能輕易抵達或擁有,,便不知不覺間怠慢了,?
那時老婆正有孕在身,短短幾天的春節(jié)假期,,回老家團聚難免奔波折騰,,于是邀請父母來長過年。正月初一,,我們闔家出游,,選擇的目標就是天心閣。
進公園大門后,,徐徐前行,,撫摸著古城墻上的窯磚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,似乎每一塊墻磚上都刻有匠人名號,,這做法彰顯的是一種嚴苛的責任與溯源吧。
令人印象深刻的,,自然還有崇烈亭,、崇烈門與崇烈塔。它們都是大有來歷的,,就是抗戰(zhàn)勝利后專為紀念長沙會戰(zhàn)中陣亡的將士所建,。崇烈門上的兩副對聯(lián)——“氣吞胡羯,勇衛(wèi)山河”“犯難而忘其死,,所欲有甚於生”,,字里行間,透露出不容輕視的堅毅與民族氣節(jié),。
后來,,去天心閣的機會就更多了,。有一兩年,兒子在旁近一小區(qū)學習吉他,。每次送他到老師家之后,,我就獨自到天心閣溜達。有一次,,太陽剛剛升起,,陽光斜穿過樹葉,在地面灑下斑駁的光影,,我蹲下身子,,在一條僻靜的小徑上,觀察一群螞蟻忙碌卻井然有序地搬運著游客遺落的面包屑,,它們那種目標專一的簡單,,我最為羨慕。
莎士比亞曾說,,一千個人眼里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,。對于同一片土地,不同的人所鐘情的面向,,各有偏好——南城天心令我歡喜的,,除了天心閣之類名勝古跡所代表的傳統(tǒng)及人文的一面,還有它的動靜皆宜,。
先說說動吧,。位于回龍山下西側的白沙古井,經(jīng)年流淌,、不溢不枯,,取水者來來往往,井沿上百態(tài)眾生……清冽的泉水無聲流淌間,,時已移,,世已變?;蛟S,只有它算得上真正的閱人無數(shù)吧,。
賀龍體育館和解放西路酒吧一條街,,則分別演繹著別樣的動感。雖然酒吧一條街的喧鬧與躁動,,于我是極不習慣的,,但是,也曾陪外地來長客人體驗過三兩次,,見識了一座城市夜生活的誘惑與性情,。
天心的靜,,在我看來,首先體現(xiàn)在點綴其間的老街巷:坡子街,、化龍池,、大古道巷、太平街,、下河街……其實,,如今信步在這些街巷,應該說沒有多少純粹的老與舊了——老是有一點,,新也有一點,;古樸摸得到,時尚聞得著,。也許,,這雜糅與并存,一切自有其內在邏輯,,真實的世態(tài)也不過如此吧,。
在南城天心鬧中取靜另一個好去處,便是簡牘博物館,。目光聚焦于一片片竹簡,,那一枚枚略扁而修長飄逸的隸體文字,總讓人忘記時間的流動,。每當在那樣的場景,,我總在想,不要低估了當年那些平凡而瑣碎的書寫,,一旦穿越時空,,傳之后世,便成為一種鮮活的證據(jù),,傳遞著事關政務,、賦稅、民生,、風俗等極為豐富的信息,;我也禁不住從內心欽敬那些竹簡整理者,工作枯燥,、甘受孤獨,,卻從未放棄對竹簡上文字的追問與解讀。
一直以為,,城市瀕水而起,,因市而興,因人而盛,但真正令其聲名鵲起的,,往往仰仗于為數(shù)不多的名人大V,,以他們的文字與事功,他們與城市的交集與軼事,,譬如孔子之于曲阜,,柳宗元之于柳州。大唐之時的杜甫結緣長沙,,就在天心,。詩圣晚年兩度駐足長沙,曾寄居江閣,,在長沙留下詩作五十余首,。
2005年開放的杜甫江閣是原址重建的,我從未登臨,,卻喜歡立于對面的橘子洲頭隔江相望,,因為我認為,這江閣,,是適宜于仰望和想象的,。
位于太平街上的賈誼故居,有一次專程去拜訪,,好像是2014年底吧,,沒料想恰好遇到閉館維修,不免有點失望,。也好,,這念想一直留著,便也是一種期盼與動力,。
當然,,這片地域上值得探訪之人,還有藥王孫思邈,、書法家何紹基,、偉人毛潤之等,以及因人而名的藥王街,、第一師范,,火宮殿、臭豆腐……
在我看來,,天心確實是一塊多面體,,總有一些美好能把你打動。至于魅力如何,,當然要靠你自己去體驗了。
>>我要舉報